
在外文系读书的时候,感觉词汇量特别贫乏的是脏话。后来听高年级同学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有785个粗口,我们没作停留就赶往图书馆。馆藏的几本塞林格后来一直呆在我们寝室,记不清轮流借了多少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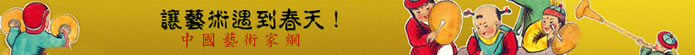
要说塞林格提高了我们的粗话水平也可以,不过,十六岁的霍尔顿挂在嘴上的也就GODDAM和HELL。老师一直对我们说读书要认真要认真,这个,我们自学塞林格的时候倒是做到了,不过,等大家集体读完《麦田里的守望者》,一致同意美国人是太容易受惊了,《麦田》哪里需要禁?
当年,脏话是我们拿起塞林格的理由,不过,《麦田》从第一页开始就有力地捕获了我们。写作课上,我们不约而同使用了“lousychildhood”,尽管童年阳光灿烂,但说一句“脏脏的童年”真是太解气了,愤怒的年龄碰上愤怒的霍尔顿,我们没像查普曼一样去枪击约翰·列侬,老师父母都该谢天谢地。
我们传阅塞林格,而他本人的沉默和隐居在我们看来真是酷毙了,对越来越脏乱差的世界,最好的批判不就是一言不发?相形之下,我们看不上为他写传记的作家、兜售他隐私的情人和女儿。“意大利面条就要下锅,罐子里有自制的番茄大蒜调味酱。再过十分钟就是我的生日,”这样的句子,作为《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的结尾,当然只能“曾是”情人了。再看看,塞林格的句子,短篇集《九故事》中,《给艾斯美写的故事:既有爱情又有凄楚》里有个小男孩叫查尔斯,他给大兵出了个谜语:“一堵墙会跟另一堵墙说什么?”
会说什么?会说什么?你得装着很费劲地猜。
“在拐弯处碰头!”
在我们青春拐弯的时候,碰上塞林格,即便他的写作范围有限,作品产量更有限,但在这个天地里达到完美的,再没第二人。所以,关于塞林格死后锁在保险柜里的十五六本书,虽然万众期待,我却心有不安。就像今天重看中文版《麦田守望者》的“译本前言”,施咸荣先生说:“我国的青少年生长在社会主义祖国,受到党、团和少先队组织的亲切关怀,既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又有丰富多彩、朝气蓬勃的精神生活,因此看了像《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的书,拿自己幸福的生活环境与丑恶环境作对比,确能开阔视野,增进知识……”这些话,多么让人伤感。霍尔顿早就不是一个美国孩子,他飘荡进我们的青春,驻留下来,但心里又特别渴望回到母亲怀抱。一堵墙已经和另一堵墙碰头,当年崇高的理想,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还在相遇的墙角吗?
至今记得二十多年前第一次看完《麦田》,学了六个粗口没处用,就在寝室里互相招呼,那时我们用得多么欢天喜地,愤怒归愤怒,但生活依然饱满,我们口中说着脏话,心里其实“愿意为了某个原则轰轰烈烈的死去”,而不是塞林格这句名言的后半句:“一个成熟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原则谦恭地活下去。”
但现在我们全都谦恭地活了下来,脏话不说了,理想也不说了,我很担心,塞林格保险柜里的那些书,相隔一世纪,和我们再次相遇,还将再次彼此见证吗?
在《给艾斯美写的故事》里,小男孩查尔斯在姐姐的信里给大兵附了一封短信,是这样的——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爱你 吻你 查尔斯
在我看来,这许是世上最温暖的一封信,也是塞林格最温暖的时刻,我希望,今天,我们打开塞林格的保险箱,会有一些查尔斯的信,而不是垂垂老矣的霍尔顿或者愤怒的小团圆。因为很显然,对今天的世界来说,最好的批评不会再是隐居式沉默,不是粗口,而是十个“你好”。
 范海龙新作展
范海龙新作展 崔明涛
崔明涛 “画水者”李
“画水者”李 “EXIN亚洲实
“EXIN亚洲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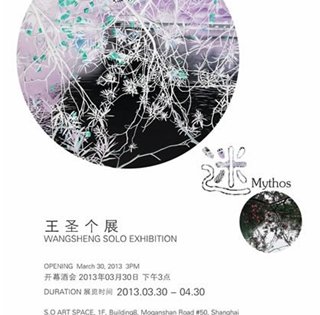 “迷Mythos”
“迷Mytho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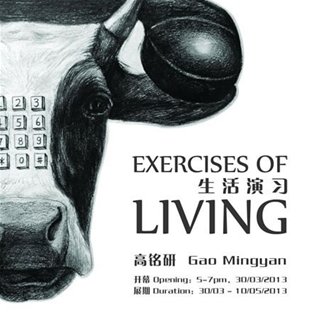 “生活演习”
“生活演习” “中国娇子”
“中国娇子” 秋冬旗袍
秋冬旗袍 脏话,曾
脏话,曾 吴冠中:
吴冠中: 艺术价值
艺术价值 2010年艺
2010年艺 09艺术转
09艺术转 美术迎春
美术迎春 身临其境
身临其境 亿元时代
亿元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