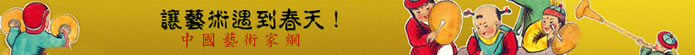
元代的文人,尤其是北方文人则远不如两宋文人那么幸运。公元1279年,当蒙古这个来自漠北的游牧民族以其悍武善战的锐势一举灭亡了长期积弱不振的南宋王朝之后,蒙元征服者对汉族封建文化的理性秩序的怀疑、漠视、厌恶乃至反对,使传统的礼治德政在这个重武力征服的政权中顿时失去了光彩,而温柔敦厚的文人便难以逃脱那被贬抑、被驱逐的厄运了。现实世界的种种冷酷与混乱使元代文人指向现实世界的进取精神大为萎缩。《渔樵记》中的朱买臣,《荐福碑》中的张镐,《冻苏秦》中的苏秦。元杂剧中失意落魄的文人形象比比皆是。我们在元杂剧中可以看到许多这种失意落魄的文人形象。与之相对照,感染了游牧文明风习的元代女性则开始彰显其枷锁拆除后的奔放个性。且不说历来被视为正面形象的敢于追求幸福的李千金(《墙头马上》),即使是历代为人所贬抑的朱买臣妻(《渔樵记》)、赵元妻(《遇上皇》),她们的弃夫再嫁,实际上也是对”地无去天之义”的一种质问。况且在我们今天看来,朱买臣妻(包括《遇上皇》中赵元妻、《金凤钗》中赵鹗妻)的叛逆之举实为情有可原:对一个封建时代的一切以家业为重的女性来说,现实需要是第一需要,如果丈夫的满腹经纶不能换回眼前的实际利益,对她们来说就是毫无意义的。这类婚变悲剧实际上是夫妻之间对生活理解不同、追求目标相异所造成的悲剧。
三、 婚变类型
正如上所述,南戏婚变戏与元杂剧婚变戏各自呈现出其不同文化体系的特色。二者婚变类型的单一与多变即为的证。
南戏婚变戏中,发生婚变的原因多是由于男主人公的负心。关于《赵贞女》,明代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篇》中记载:”即旧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实为戏文之首。”《赵贞女》之所以被称为”戏文之首”,研究者多认为是因《赵贞女》为人们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温州杂剧”(南戏的滥觞)。
此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即《赵贞女》开启了南戏多婚变题材的传统。这种悲剧形式显然很受民众欢迎,其后的南戏作品《王魁负桂英》、《三负心陈叔文》、《崔君瑞江天暮雪》、《王俊民休书记》、《临江驿》、《李勉负心》、《王宗道负心》几乎都是按《赵贞女》的情节模式加以敷演的。
早期南戏婚变戏题材直接来源于民间传说,又不加修饰地在舞台上再现了统治阶级所忌讳的东西。如《赵贞女》中的蔡伯喈,对父母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在普通民众眼里,是个忤逆不孝的子孙;他对糟糠之妻采取”马踹”的残忍暴行,又是不义小人。让蔡伯喈最终得到”雷轰”的报应,是民众惩恶扬善愿望的自然流露,它反映了文人染指南戏之前南戏质朴的民间趣味。徐渭说《赵贞女》为”里俗妄作”,正反映出这类作品的民间性。
《张协状元》则显示出南戏婚变戏由质朴向文人化的过度。翻开《张协状元》,第一出就由末角出场,声明”但咱们,虽宦裔,总皆通”,后又”再白”:”《状元张协传》,前回曾演,汝辈搬成。这番书会,要夺魁名。”这里传达出两个信息:其一,这本《张协状元》是由”宦裔”改编《状元张协传》而成。这”宦裔”是何身分呢?副末唱过诸宫调后,生扮张协上场,向观众交代:”真个梨园院体,论诙谐除师怎比?九山书会,近日翻腾,别是风味。”可知《张协状元》的作者是九山书会的”书会才人”。书会才人是宋元时代的产物,他们具有书生与平民的双重身分。其二,在《张协状元》前就已有《状元张协传》存在,并且曾经引起轰动,《状元张协传》的原本虽未保留下来,但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第五出王金榜谈到戏名时,就有”张协斩贫女”之句,南戏《崔君瑞江天暮雪》存曲中也有”负心的是张协、李勉,到底还须瞒不过天。天,一时一霎丧黄泉。便做个灵魂,少不得阴司地府也要重相见”。从中我们可以探出,早期张协题材的作品中,张协路经五鸡山时不仅有剑刺贫女的行动,而且贫女因此便”命丧黄泉”了,并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团圆结局。我们很轻易就可以发现,早期的张协题材作品也和《赵贞女》、《王魁》等一样,是谴责书生富贵变心的。然而到了《张协状元》作者这里,由于作者实际上也和张协一样,与科举制有着难分难解的情结,这决定了他们在改编《状元张协传》时,作为市民阶层的一部分,他们保留了”里俗妄作”的早期南戏中对书生的否定性评价,但对书生的不自觉心理倾向又使他们试图绕开导致书生负心的根源——科举制度。因此,他们不惜竭力”翻腾”旧作,通过改贫女”家贫世薄”卑贱身分为宰相义女的方式,生扭成二人的大团圆结局。虽然如此,整部作品依然处处流露出作者对张协薄负心行为的谴责,只不过较之《赵贞女》、《张协状元》显得隐蔽、含蓄一些,把揭露和批判注入了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之中。《张协状元》的出现,标志着南戏创作已趋成熟,对后期南戏婚变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南戏中还有一类特殊的婚变模式,即”一夫二妻”模式,今传《刘知远白兔记》和《琵琶记》两本。
《刘知远白兔记》虽是敷演五代后汉开国之君刘知远发迹变泰的历史故事,但与《新五代史》中的简略记载相比,《刘知远白兔记》显然增添了许多民间传说与艺人渲染的成分,这使得一段帝王发迹的史实逐渐演化成了一部反映刘知远与李三娘悲欢离合故事的婚变戏。
与《赵贞女》、《王魁》、《张协状元》等明显为谴责男子富贵变心的婚变戏不同,《刘知远白兔记》作者对刘知远隐瞒家中有妻、重婚岳氏的行为不见有任何非议,相反倒在《见儿》一出里极力渲染刘知远对”恩妻”的思念之情,以及岳氏的贤惠大度。尽管在《忆母》一出中,已长至十六岁的咬脐郎当面揭露了父亲负心的实质:”继母堂前多快乐,却交亲母受孤凄。爹爹,忘恩负义非君子,不念糟糠李氏妻”,但作者紧接着又让岳氏出场,”深明大义”地提出接李三娘来家,”同享荣华,愿为姐妹”。可见作者似乎并不以刘知远重婚岳氏造成事实上产生婚变为意。作者更为关注的是刘知远的发迹变泰过程和家中李三娘忍辱负重、誓不改嫁的坚贞,并对”一夫二妻”的团圆结局极为欣赏。这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下层民众心理。据成化本《刘知远白兔记》第一出末云:”这本传奇亏了永嘉书会才人,在此灯窗之下,磨得墨浓,蘸得笔饱,编成此一本上等孝义故事。”这段话表明《刘知远白兔记》的主旨非但不是谴责男子富贵变心,反而是表彰子孝夫义的。《刘知远白兔记》的作者为永嘉书会才人,也就是下层知识分子,在当时地位是极其低下的,周密《武林旧事》就将他们列入”诸色伎艺人”中。此外,《刘知远白兔记》的文辞虽历经明人改动,仍可见出其俚俗古质,富有民间特色。不仅文辞,《刘知远白兔记》的思想也是接近于下层民众的:历史上的刘知远在公元946年从石重贵手里夺取政权,改”后晋”为”后汉”后,第二年便让位于其子。这段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湮没无闻的发迹变泰故事,在民间传说中却得到一再渲染。它反映了民间对帝王的崇拜,尤其是对起于草寇的平民帝王的崇拜。如戏中李大公见到卧在蓬蒿中的刘知远”鼻息如雷振”、”气如吐虹”,”更有蛇穿窍定须显荣,振动山河鱼化龙”;岳节使举板子欲拷打刘知远,也见”空中五爪金龙”。刘知远形象被一步步神化了。刘知远由落魄潦倒的流浪汉而发迹,这一故事情节本身就会令身为平民百姓的作者油然而生艳羡之情。刘知远的发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们的理想。在这样的前提下,刘知远重婚岳氏的负心之举在他们看来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他们干脆放弃了为男子洗脱的工作而强调所谓”天意”。当然,对李三娘的受尽磨难,善良的民众也愿意她脱离苦海,得到好报。这样,子孝夫义、一夫二妻自然是他们能想象到的最圆满结局了。
另外一本”一夫二妻”式南戏婚变戏是元末高明据《赵贞女》而改编的《琵琶记》。徐渭《南词叙录》指出:高明”惜伯喈之被谤,乃作《琵琶记》以雪之。”因为历史上的蔡伯喈(名邕)以孝闻名,《后汉书》中记载他”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为蔡邕雪谤,应该是高明改编《赵贞女》的一个主要动机。
经过高明的改动,《赵贞女》中弃亲背妇的蔡伯喈,成了不忘父母发妻的孝子义夫。蔡伯喈重婚不归,也是由于辞官、辞婚不成。最后的结局,也由”马踩赵五娘,雷轰蔡伯喈”改为一夫二妻团圆。《琵琶记》是南戏由民间文学过渡到文人创作的转折点,也是南戏婚变戏由无意识地回护男子负心(如《刘知远白兔记》)变为有意识为其辩解的开始。然而由于《琵琶记》中又确有蔡伯喈对父母”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对赵五娘”停妻再娶妻”的客观事实存在,无论作者如何精心掩饰,也不能避免情节上的不能自圆其说。李渔《闲情偶寄》曾评之曰:”元曲之最疏者,莫过于《琵琶记》,无论大关节目,背谬甚多——如子中状元三载,而家人不知;身赘相府,享尽荣华,不能遣一仆,而附家报于路人;赵五娘千里寻夫,只身无伴,未审果能全节与否,其谁证之:诸如此类,皆背理妨伦之甚者。”可见,《琵琶记》客观上还是一部反映书生富贵易妻的婚变戏。
从《赵贞女》、《琵琶记》、《张协状元》一直到《琵琶记》,我们发现,南戏婚变戏由最初的反映男子负心遭天谴到始于负心而终于团圆最后到不得不负心而一夫二妻团圆,表现出一种越来越维护男子利益的趋势。这既表现出南戏婚变戏经历了一个由民间化向文人化转变的过程,同时也是由宋至元南方地区时代思想的折光。宋代科举制度造成大量的富贵易妻事实自不必说,到了元代,虽然南方地区早已形成相对凝固的地域文化特征,然而由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语),南方文人也和北方文人一样,不免遭受沉抑下僚的打击。文人地位的陡落,使他们更急切地要寻求自慰的方式。在这种情形下,再唱书生负心遭报应的老调,显然已不能满足他们的自我怜惜需要了。
这样,南戏婚变戏中的书生也就由被否定被谴责的对象逐渐变而为受到同情甚至歌颂的对象了。
然而,从类型上看,除极少数历史传说题材的作品(如《朱买臣休妻记》、《乐昌公主破镜重圆》)以及由元杂剧改编而来的作品(如《拜月亭记》)以外,南戏婚变戏可以说只描写了一种婚变形式,即”富贵易妻”,其原因正如钱南扬先生所说:”不是为财,就是为势”。而元杂剧婚变戏则反映了各阶层人物形形色色的婚变问题,包括贵者负贱型(如《潇湘夜雨》、《秋胡戏妻》)、弃夫再嫁型(《渔樵记》、《金凤钗》)、商人插足型(如《青衫泪》、《百花亭》)、长辈逼离型(如《墙头马上》、《拜月亭》)、强人骚扰型(如《鲁斋郎》、《生金阁》)、通奸陷害型(如《燕青博鱼》、《村乐堂》)等。与南戏婚变戏性质的一成不变相比,元杂剧婚变戏的复杂多变显然正是北方地区两性关系新气象的反映。
四、 婚变内涵
同是婚变,南戏和元杂剧的内涵并不相同。南戏婚变悲剧更多地带有封建伦常的标记。蔡伯喈出门赶考后,赵贞女在家竭力奉养公婆,替蔡伯喈实施礼教规定应由儿子行的”孝”,因而是有恩于蔡伯喈的。王魁落魄时,是桂英将他收留,为他置办四时之需。张协也是进京赶考时,路遇强人,财物尽失,人被打伤。是贫女救了他,朝夕服侍,并卖掉头发为他筹措进京盘缠。没有贫女相助,张协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否极泰来的。刘知远未发迹前,窘至偷庙中福礼充饥。是李大公将他收留,并将女儿李三娘嫁给他。刘知远从军一走十五年,三娘在家受尽恶嫂折磨也誓不改嫁。刘知远再婚,无疑也是忘恩负义之举。综观这些婚变悲剧,我们看到作者实际上是代表民众表达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传统伦理观念,即”义”的道德主题,否则就是”负义”。在这些婚变戏中,负义(或曰负心、负情)与否,决定于曾受恩惠的一方有没有给对方以相应的价值补偿,而爱情实际上被置于作者的道德体察之外。负情,与其说是负于”爱情”,毋宁说是负于女方的”恩情”。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南戏婚变戏的男女主人公当初的结合也有爱情的成分在里面,但这种夹杂着施恩与受恩成分的爱情与现代意义的爱情是有明显区别的。
造成南戏婚变戏中这种婚变格局的原因,正是女性历史地位的低下。恩格斯曾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女性从此处于无力自救、任人宰割的地位。若想改变这种状况,只有依附于地位高于自己、或有发迹潜力的男子。桂英即寄希望于王魁得第后改变自己的风尘女子身分;李大公也是发现刘知远有发迹之相后决定将三娘嫁给他的,带有明显的投机心理。与之相比,赵贞女、贫女的功利性虽不那么明显,然而她们的贞顺贤淑,犹如不争之争,更显出她们的可怜与不幸,从而博得了社会巨大的同情。但社会现实是残酷的,企图依赖于男子——而不是改变自身——来摆脱眼下的境遇,其结果有时比原来的处境更坏。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只要女性在婚姻中的依附地位不改变,这种婚变悲剧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于社会生活之中。后期南戏婚变戏的团圆结局,只不过是表达了作者的善良愿望罢了。
在元杂剧婚变戏中,我们则能看到比赵贞女、贫女、李三娘要热烈泼辣得多的众多女性形象。如《调风月》中的燕燕,《渔樵记》中的玉天仙,《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甚至《替杀妻》中的员外妻。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与南戏婚变戏中的女主人公基本处于被选择地位相比,元杂剧婚变戏的女主人公往往表现出一种积极主动的精神,甚至有时还拥有婚姻决定权,如《秋胡戏妻》中的罗梅英,不顾父母的胁迫,坚决不改嫁张大户;发现在桑园调戏自己的竟然是阔别十年的丈夫秋胡后,悲愤交加,不肯认丈夫。
《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在对裴少俊一见钟情后,当晚就约裴少俊在后花园私会,被嬷嬷发现,又当机立断和裴少俊私奔。《燕青博鱼》中的王腊梅,《酷寒亭》中的萧娥,《货郎旦》中的张玉娥。虽然被打上了”淫妇”烙印,但她们的由对现实婚姻不满而生的主动寻求出路,比之逆来顺受、终身被囚于无爱婚姻牢笼中而麻木不知的女性,多少总显示出了其主体意识的觉醒,其精神实质和潘金莲、安娜•卡列尼娜一样,”既是有罪的,同时也是无罪的”(别林斯基语),她们也和元杂剧中的众多女性形象一样,带有元代女性特有的”野性”色彩——富有胆识、敢作敢为,少有封建伦理道德的羁绊。从这类女性群像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草原文化撞击下元代女性强大而热烈的生命冲动,这一点我们应该加以肯定。
 范海龙新作展
范海龙新作展 崔明涛
崔明涛 “画水者”李
“画水者”李 “EXIN亚洲实
“EXIN亚洲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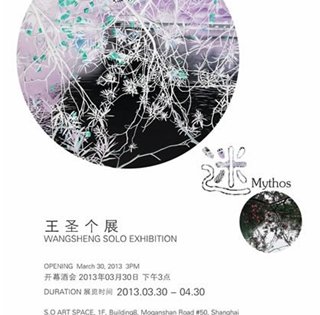 “迷Mythos”
“迷Mytho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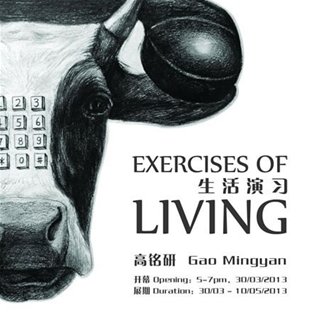 “生活演习”
“生活演习” “中国娇子”
“中国娇子” 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 中国戏曲
中国戏曲 北昆耆宿
北昆耆宿 潮剧的演
潮剧的演 景物造型
景物造型 服饰造型
服饰造型 戏曲文物
戏曲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