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梅戏是从乡村小戏发展而来,《闹花灯》和《打猪草》是黄梅戏早期乡村小戏中最具代表性的剧目,安庆各地现在还有”天天打猪草,夜夜闹花灯”的说法。早期黄梅戏老艺人不同的口述唱本,胡遐龄口述本《闹花灯》、余海先述录本《夫妻观灯》以及陈宗江口述本《打猪草》、余海先述录本《掰竹笋》,是我们能找到的这两个小戏最原始的文本。这几份老艺人的口述本,比起经五十年代改编的《闹花灯》和《打猪草》,更接近原生态。由于无法判定不同口述本的演出背景,我们只能以改本为参照,比较两份口述本与改编后版本的不同。为方便起见,下文将胡遐龄口述本《闹花灯》及余海先述录本《夫妻观灯》及改编后版本《闹花灯》统称胡本、余本及改本《闹花灯》,将陈宗记口述本《打猪草》及余海先述寻求《掰竹笋》及改编后版本《打猪草》统称陈本、余本及改本《打猪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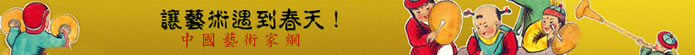
先看《闹花灯》。与改本相比,余本和胡本有大量生旦逗趣的对白,这些对白多以谐音造成的插科打诨为主,改本中,插科打诨的对白被删除,如余本和胡本开头都有夫妻隔门对白,且都有生将”裹足”故意说成”裹粽”的细节;夫妻相见后,余本和胡本又都有一大段戏谑性对白,现引余本中的一段:
李荷花(白)当家的,你在哪里呢?王小中(白)我盘里滚到沟里。
李荷花(白)敢是城里到州里。
王小中(白)不错。
李荷花(白)你也看见什么世景么?王小中(白)我看见个五人轿。
李荷花(白)四人轿。
王小中(白)中间坐个小贼。
李荷花(白)坐个老爷。
王小中(白)不错。他前面有一对夜不收。
李荷花(白)衙役头。
王小中(白)不错。他挡到我们的尿路。
李荷花(白)你挡到他的道路。
在改本中,这些逗趣的因素统统消失。除插科打诨的对白被大量删除外,生旦的唱词也遭到大幅度的删改,余本和胡本中旦角出场时唱的开门调都比改本中的复杂得多,且有一些粗俗淫秽的暗示,现以胡本中唱词为例:奴在房里绣荷花,呀呀子哟,看见蝎子墙上爬,喂却喂却一喂却,喂却我的冤家郎呀哈哈,伸手去拿它呀哈呀。蝎子咬了我的手,呀呀子哟,又痒又痛又酸麻,喂却喂却一喂却,喂却我的冤家郎呀哈哈,从后不拿它,呀哈呀。
夫妻观灯之前,胡本和余本都有夫妻进庙求子的仪式表演性唱段,这一段唱词在余本和胡本中几乎相同,但在改本中不再有。此外,两个口述本都有以各朝代历史典故和历史人物故事描述花灯的唱段,胡本从周朝、三国一直唱到唐、宋、元、明、清,余本中从周朝和三国唱到唐、宋,这些带有历史戏说意味的民间意识形态性唱词在改本中只简化为周朝和唐朝的灯,仪式性因素与意识形态性因素都做了大幅度删改,这无疑是官方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
除对白与唱词大量删改外,改本对表演部分也作了修改。余本和胡本《闹花灯》中均有旦角看灯时因被人踩脚跟和踩掉鞋而三番两次撒娇生气不愿看灯的表演。改本将这段表演简化成妻子见有人不看灯而看她因此撒娇生气不愿看灯。
口述本中被删改的还有粗俗的骂人话和鄙陋的俚语、俗语。余本中当王小中唱”不好了,不好了,荷花的裤子被火烧了!”,李荷花吓得又看又摸自己的裤子,唱道:你拆白的鬼,哄老娘,活活的把我的魂、魂吓掉、胡本中的王妻唱的则是:吐脓的,吐血的,险些儿把奴魂吓掉。“拆白的鬼”、”吐脓的”、”吐血的”,都是安庆方言俚话中较为恶毒的骂人话,改本中改为家人之间常用的亲昵骂人话”砍头的”。
与《闹花灯》改本对对白、唱词与表演中大量情节进行删改相类似;《打猪草》的改本也更为简洁、精雅。余本和陈本《打猪草》都有旦角”偷笋”的行为和生角”偷牛”的历史,都有”要钱”、”赔钱”、”掰笋”、与”拜老庚”的情节,改本中”偷牛”、”掰笋”、与”拜老庚”‘都被删去,”偷笋”改为”碰笋”,”赔钱”改为”赔笋”;而这些被删改的情节恰恰集中了大量生旦调笑逗趣的科诨因素与粗俗戏谑的唱词,如余本《掰竹笋》中”拜老庚”一段:
金三伢(白)你么年生的。
陶四女(白)甲寅。
金三伢(白)你嫁人,就嫁我。
陶四女(白)呸、我甲寅年乙卯月生的。
金三伢(白)是我心下一喜,我说你嫁人就嫁我。
改本《打猪草》除保留陈本和余本的精华部分——对花调外,其他细节因素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删改。与情节删改相对应的,是文辞的雅驯。改本中对”活妖婆”、”死不要脸的东西”、”贼婆娘”、”小婊子”等骂人话也作了润色加工,陈本和余本中带有戏谑与挑逗、暗示性的对白和唱词都经过剔除与加工,原本较为粗糙的唱词也更加对仗、齐整,这样,《打猪草》原来粗俗戏谑的风格变得清新雅致,俨然一幅纯净美好的乡野风俗画和一对善良厚道的乡村小儿女。
二
对民间口述剧本的记录、加工、润色、整理,是一个”文化过滤”过程。其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孔子删《诗》。葛兆光谈到这一传统时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删诗”传统等人为的作用,社会历史文献经”‘意识形态’、’精英意识’、’道德原则’、’历史学叙述’等几重筛子的选择、编辑、写作、评述”,早己失去其原初的本原面目,只剩下其”硬体部分”的形状、结构或其大致迹象的遗存。倘若把老艺人的口述本当作相对原生态的黄梅戏形态,我们看到,改编后的《闹花灯》、《打猪草》情节更紧凑集中,对白与唱词更精雅工整,表演也更规范,老艺人口述本中插科打诨式因素、粗俗的骂人话和戏谑的动作,以及仪式性与民间意识形态性唱词都被删除或更改,只保留了原唱本”化石”的”硬体部分”,如《打猪草》中的”对花”和《闹花灯》中的”观灯”。在这里,我们选择黄梅戏作为切入点,以黄梅戏相对具有乡村原生态形式的剧目《闹花灯》和《打猪草》为个案,不仅仅是因为黄梅戏具有从乡村地方小戏迅速发展壮大成全国性大剧种的特殊历程,更是因为我们现在依然可从黄梅戏小戏中辨别黄梅戏相对原生态的特征,此外,早期老艺人的口述本也使我们更贴近其原生态。
就戏曲这种以说唱为主要形式的民间艺术样式而言,它本是民间艺人口耳相传肢体相习的表演艺术,由于文人的介入与参与,戏曲始而”文字化”终而”文士化”。这样一来,戏曲就失去了原初的面貌。
“关于经验的记忆可以活在戏剧中,一旦翻译成流传的句子,就隐含着僵化成缺乏鲜活印象的书页的危险。”我们不仅有文人的”删诗”传统,更有官方的”禁戏”传统,”删诗”与”禁戏”遂成为戏曲的双重过滤器,使戏曲的外在状貌和内在功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异,我们对戏曲的认识也越来越偏离其原生态样式而忽略其被遮蔽的一面。为使我们的研究不再是滞后的”化石”研究,我们有必要回溯本原,追踪戏曲的原生态,研究戏曲原生态形式的变异。由于戏曲的说唱表演特征,其存在形态就是一个永远处于流动和变异中的过程,因此,我们的研究就只能是相对原生态的研究,绝对的原生态形式由于难以确定其具体的状貌不可能成为研究的对象。
联系黄梅戏一度遭”官禁”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官禁”的尺度正是黄梅戏改编的尺度,即剔除官方意识形态观念中不健康的、有伤道德风化和有碍礼仪秩序的因素,经过删改加工,相对原生态黄梅戏在”文字化”的基础上越来越”文士化”,删改的过程就是过滤与提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黄梅戏相对原生态的形式发生了变异,原唱本中插科打诨式因素、粗俗的骂人话和戏谑的动作、仪式性与民间意识形态性唱词为规范化、雅驯化的成熟戏曲脚本替代,而插科打诨式因素、粗俗的骂人话和戏谑的动作、仪式性与民间意识形态性唱词是乡村原生态地方戏最具本质性的民间狂欢仪式的体现,是乡村原生态地方戏的内核。
“狂欢”一词在中国词典中只和西方的”狂欢节”即”谢肉节”联系在一起,而”狂”在中国向来是带有贬义色彩的,它的本义指狗发疯,后泛指人疯狂。受巴赫金狂欢诗学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各领域尤其是民俗学、人类学领域才开始发现”狂欢”作为语义学概念与范畴在中国民俗文化领域大范围的存在。从子贡向孔子描述蜡祭”一国之人皆若狂”的情景至今,对民间祭祀仪式演出场景与传统民俗如社火、庙会等活动的描述常与”狂”联系在一起,但由于官方”仪”与”礼”的约束,我们很少将”狂”与”欢”相提并论。从戏曲本身的发展来看,倘若它褪去了乡村原生态的本来面目,成为文人案头阅读的剧本和士大夫化、宫廷化的精雅演出,谁还能看出它的民间狂欢仪式本原呢?较之改编后的《闹花灯》和《打猪草》,黄梅戏老艺人的口述本更具有相对原生态性,而相对于黄梅戏后期日益精雅化的文人创作如《天仙配》、《女驸马》乃至更晚一些的《龙女》、《徽州女人》,即使是经改编了的《闹花灯》和《打猪草》也更具相对原生态性,其相对原生态性最明显的体现是从演出形式到演出内容诸多因素无所不在的狂欢化色彩。
从口耳相传、人人参与的民间娱乐狂欢活动到具有一定师承关系的职业与非职业性演出,从乡村到城市、从本地到异乡、从地方小戏到全国性剧种,黄梅戏每走动一步都意味着由俗到雅、由边缘到中心的努力与挣扎,在这努力与挣扎中,黄梅戏最初的民间狂欢仪式逐渐弱化,而相应的戏曲审美因素一步步加强,老艺人口述本《闹花灯》和《打猪草》的删改便是这一过程的充分体现。
在巴赫金的狂欢诗学中,狂欢是源于狂欢节仪式——演出形式的狂欢节式世界感受,而狂欢节仪式——演出形式是民间诙谐文化的一种基本表现形式。民间诙谐文化与官方严肃文化相对立,具有包罗万象性、与自由不可分割和与非官方民间真理的重要联系,其审美观念为怪诞现实主义。怪诞现实主义以物质、肉体因素为自然因素,其主要特点是降格,即贬低化、世俗化、肉体化,怪诞的人体观念是怪诞现实主义的基础,而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怪诞风格充满了狂欢节的世界感受,因此,怪诞风格与民间诙谐文化和狂欢界世界感受完整世界不可分离。
巴赫金的狂欢诗学建立在西方民间广场文化的基础上,是西方民间传统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折射,狂欢诗学着重表现狂欢式世界感受。我们这里所指的则是乡村地域范围内作为戏曲发生学意义的民间狂欢仪式及其在审美化精雅化戏曲形态本身的遗存。侧重于狂欢式生存体验。
虽然文化背景和观照视角不同,狂欢的形式和本质却没有差别。《闹花灯》和《打猪草》改本中被删除的插科打诨式因素、粗俗的骂人话、戏谑的动作、仪式性与民间意识形态性唱词是民间狂欢仪式在乡村原生态戏曲中的反映。狂欢是一种突破了等级、界限与规则和秩序的活动,乡村世界的狂欢与娱乐有着本质上的亲缘关系,其狂欢的时空也极为有限。
除娱乐狂欢的功能外,祭祀仪式也是其主要功能之一。正是在娱乐和祭祀仪式的结合中,狂欢式生存体验才被释放出来,并找到相应的载体得以呈现。
插科打诨式因素以丑角表演的形式表现,常与粗俗的骂人话、戏谑的动作联系在一起,它们不仅是娱乐狂欢活动的集中体现,更是乡村生活原生态形式的形象化展示。的确,即使是在现在已被文明彻底浸透的乡村,乡野村民们仍然熟稔于这样插科打诨式的逗趣调笑,在这调笑中往往伴随着粗俗的骂人话与戏谑下流的动作。这是乡民远离官方意识形态中心,在一定自足空间内不拘言语行为方式的有限自由生存,这样的生存方式一旦与节庆娱乐、与祭祀仪式相结合,就渗入了仪式表演与娱乐狂欢的因素,成为生活与表演的合一,成为对生活原生态的变形与夸张。
由于生活与表演的合一,由于仪式表演因素和娱乐狂欢因素的整合,戏曲便成为仪式表演与娱乐狂欢的当然载体,戏曲的扮演本质、戏曲具体言语动作既超越现实又摹拟现实的表现方式为乡村娱乐狂欢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承载空间。
 范海龙新作展
范海龙新作展 崔明涛
崔明涛 “画水者”李
“画水者”李 “EXIN亚洲实
“EXIN亚洲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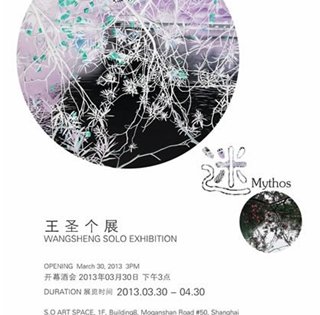 “迷Mythos”
“迷Mytho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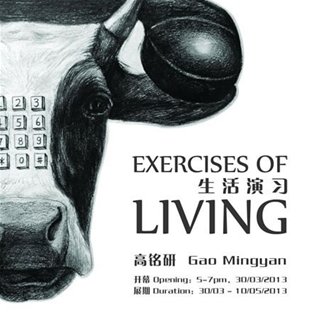 “生活演习”
“生活演习” “中国娇子”
“中国娇子” 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 中国戏曲
中国戏曲 北昆耆宿
北昆耆宿 潮剧的演
潮剧的演 景物造型
景物造型 服饰造型
服饰造型 戏曲文物
戏曲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