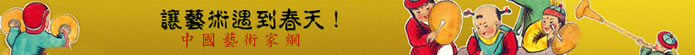
至于“对歌”、“盘歌”等的盛行,则更是给了黄梅调的戏剧定型以实质性影响。
张紫晨在《歌谣小史》中写道——
在清代,对唱山歌的形式也很盛行……男女青年在表达爱情时多用互相答唱。儿童之间为了游戏也常常互相对歌数唱。就是一般成人中用山歌互相问答,盘诘和交流各种知识也极普遍。
这里,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山歌”由前一阶段的个体抒情叙事(即便是群体演唱,它的叙述方式还是个体的,如“妹”如何如何,“郎”如何如何,以独立人物贯穿全篇),已发展出了此时的“二元”对答的叙事,使其超越“十二月体”的时序结构模式。通过第二叙述因素的引入,可以在空间意义上展开结构。这实质上是对戏剧境界的实质性迈步,相当于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首次使用“第二个演员”一样,使本属叙事“文学”范畴的歌谣有了戏剧的品貌。由此,作为戏剧本质之一的“动作”得以产生,对立(冲突)、互补(交流)成为可能,事件的形象(表演)展开有了载体。这种“对歌”、“盘歌”,在乾嘉之际的盛行,为黄梅(采茶)调的以歌入戏,并藉此完成戏剧定位提供了保障性前提。由此,我们看到,黄梅戏在向“近代”民间歌谣取养的过程中,逐渐从“个体抒情”的“自叹”中超越出来,引入“盘歌”、“对歌”的冲突互补因素,衍化出一大批“二小”、“三小”戏。当然,民间歌谣的“对歌”、“盘歌”,其对立因素更多地是为了叙事和结构的需要,是展开叙事的媒介,抒发情绪的载体,如:“啥为天上三分白?啥为天上一点红?啥为天上悬空挂?啥为天上锦包拢?天公下雪三分白,日落西山一点红,南北星斗悬空挂,乌云接日锦包拢。”等等,实质上是一种抒情方式,是文学性的问答结构。故此,由它影响而成型的黄梅戏早期小戏尽管也有对立因素的引入,但冲突却不是主要的,而是藉此构成一种歌舞抒情,对答叙事的结构体制。这从另一方面使我们看到“近代”民间歌谣对黄梅戏生成的决定意义。人们所普遍熟悉的黄梅戏传统小戏《打猪草》、《闹花灯》、《三字经》、《打哈叭》、《瞧相》、《胡延昌辞店》、《戏牡丹》等,实质上就是这种“对歌”、“盘歌”的产物,有些甚至就是对“互相问答”、“盘诘和交流各种知识”的清代“对唱山歌”的直接借用,如《打猪草》中的“对花”即是。据我们所知,《桐城歌》中有不少这类“男女对答”的歌谣,像《表桐城》、《乖姐与黑郎》、《妹子跟我保快乐》等已基本是“男女交流”的表演唱。这些无疑都会对进入此一地区的黄梅调发生深刻影响,助其完成向戏剧的过渡。
说“近代”歌谣的盛行为黄梅戏的生成提供契机,除了上述叙事功能、结构模式及角色体制的影响外,民间歌谣的语言及故事 (或题材)本身也是黄梅调可以拼命吮吸的不竭甘泉。如《桐城歌》的《妹子跟我保快乐》中关于“多”的男女对唱就与黄梅戏传统小戏《闹花灯》中王小六夫妇关于“灯”的对唱,在情趣及修辞手法上颇为相似。请看——
《桐城歌》 黄梅戏
女 玩狮子 妻 观长的
男 看的多 王 是龙灯
女 你头上 妻 观短的
男 毛不多 王 狮子灯
女 我头上 妻 蟹子灯
男 虱子多 王 横爬行
女 做婆婆 妻 虾子灯
男 嚼经多 王 犁弯形
女 做媳妇 妻 鲤鱼灯
男 受气多 王 跳龙门
…… ……
这里均为女提问男回答,且以三字为句,多重音叠韵,可见黄梅戏剧本文学的浓重的民歌印痕。据不完全统计,在黄梅戏传统剧目中来自民歌民谣,或明显受到民歌民谣影响的就有小戏《姑嫂望郎》、《买杂货》、《山伯访友》、《瞎子闹店》、《剜木瓢》、《恨大脚》、《绣荷包》、《打猪草》、《闹花灯》及前面提到的“自叹系列”等20余个和大戏《乌金记》、《白扇记》、《花针记》、《卖花记》、《丝罗带》、《菜刀记》等10余出,几占黄梅戏传统剧目总数的三分之一!“近代”民间歌谣的深厚影响,“近代”民间歌谣在安庆沿江一带的盛行,使黄梅调一人安徽便获得了文学姻媾,从而迅速生成极富民间性的歌舞品貌的黄梅戏。就黄梅戏传统剧目而言,其不仅在情调、题材、内容上呈现民间歌谣的明显“遗传”,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深受民间歌谣的濡染。有相当一批传统剧目纯唱无白,或仅几句白口,如《送绫罗》、《卖花篮》、《卖杂货》、《卖疮药》、《买胭脂》、《胡延昌辞店》、《吕蒙正回窑》等,不仅是“近代”民间歌谣的折光,也体现了《孔雀东南飞》叙事歌咏的深厚传统。
说“近代”民间歌谣给了黄梅戏的生成以文学孵化,还是基于“近代”民间歌谣本身已具有的某些戏剧性倾向。进入安徽的黄梅调一旦需要在戏剧上凝结,就能便利地找到民谣对应。从民谣中取采文学,无意中得到了久久渴望的戏剧信码。二者一经融合,便立刻生成了戏剧意义的演出形态。
据关德栋先生研究,“明刊戏剧选集《万曲长春》卷四”就曾把民歌《挂枝儿》收人其中,“《弦索调时剧新谱》”也纳其入谱。把民歌收入“戏曲”选集,足见当时的民间歌谣与戏剧的相同与相通。例如“雨潇潇风细细香闺寂静,灯闪闪影茕茕独靠云屏”之类的曲词与成熟形态的戏曲唱词已几无二致,体现了抒情与叙事兼容的剧曲风格。而“鲁智深游戏在山门外……忽听得山下有个卖酒的来,酒保,你挑上山卖与洒家,吃个爽快,……”则简直就是个微型戏曲表演唱,体现了角色分工,表演者以角色身份自居等多种戏剧要素。京剧的《醉打山门》便由此而来。《桐城歌》中的《太平灯歌》更是如此,其不仅有白有唱有对答,且有行当有装扮,人物以角色自居,表演者有了明确分工,如“吾神三天门下赵公明是也”,已进入代言体境界。藉此,我们可以见出,明清之际的江淮之地(“两淮以至江南”),民间歌谣不独在数量上建构了辉煌、风靡一世,而且在质量上也独占鳌头、尽得风流。前者给“近代”民间戏曲以氛围裹卷、境遇包孕,后者则给“近代”民间戏曲以实像取摹、格范映照。对于安庆沿江一带来说,“近代”民歌的风骚独领、红极一时,遂使得这块土地浸透了民间文学的汁液,负载了足够的戏剧信息。如此,湖北黄梅的采茶调所苦苦寻找钓文学伴侣终于在安徽安庆(一带)邂逅相逢。它们彼此拥抱,相见恨晚,一遇而不可分离,使得黄梅调再也不用“手捧唱本”“边看边唱”了,迅速获得了“演”的品格,完成了由“黄梅歌”向黄梅戏的整体位移。由此,“近代”民间歌谣使黄梅戏在安徽境内得到了质的规定。
戏剧批评史家夏写时先生曾以“黄梅戏《红楼梦》,时有淳朴的安庆、凤阳风情”来认定它的“迷人”风采。这里,所谓“安庆”、“凤阳风情”实质上就是一种导源于桐城歌、凤阳花鼓为代表的安徽民间歌谣的民俗艺术精神,导源于“近代”民间歌谣的乡土文化传统。
黄梅戏由此走向新天地。
 范海龙新作展
范海龙新作展 崔明涛
崔明涛 “画水者”李
“画水者”李 “EXIN亚洲实
“EXIN亚洲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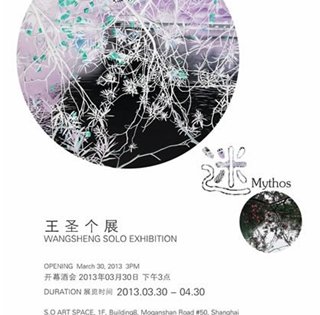 “迷Mythos”
“迷Mytho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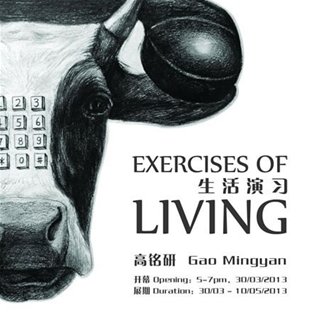 “生活演习”
“生活演习” “中国娇子”
“中国娇子” 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 中国戏曲
中国戏曲 北昆耆宿
北昆耆宿 潮剧的演
潮剧的演 景物造型
景物造型 服饰造型
服饰造型 戏曲文物
戏曲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