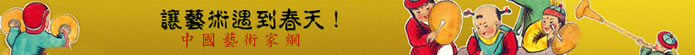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说:”三者,天地人之数。”《说文》说:”三,天地人之道也。”“三”的这种特殊的文化因素的哲理化倾向便成为群聚意识中的神秘模式,并且出于意识或因袭模式的原型不断浮光掠影地繁复衍生出各种以”三”结构基础的文化形态,推衍出种种彪炳千古、流芳万世的文化遗产。
无独有偶,T·丹齐克《数:科学的语言》说:”南非洲的布须曼(Bushmen)族。除了一,二和多之外,再没有别的数字了。”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说:”在非常多的原始民族中间(例如在澳大利亚、南非一些地方)用于数的单独的名称只有一和二,间或还有三。超过这几个数时,土人们就说:许多、很多、太多。”并说”在安达曼群岛,尽管语言词汇非常丰富,数词却只有两个,”和2。3的意思实际上是-多一个.。”从以上的说法上看,对”三”的理解,即解释为”许多”,而不是定数词;或表示为”多一个”的意思。
《易经》内标记体系,鉴于三和六之上,六是三的二倍。八卦系由三横线(称之阳爻)及中断横线(称之阴爻)组成,六十四卦就是由六条横线和中断横线交错组合构成,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它们都是三的倍数。正因于此,才演绎出”三通鼓”的惯例习俗。六十四卦中第五十卦,为鼎卦,是唯一的工具、用具命名的卦目。这一卦目揭开古代多以”三”为词冠的奥秘。南宋·陆九渊说:”天地人为三才,日月星为三辰,卦三画而成,鼎三足而立,”《史记·武帝记》:”禹收九收之金,铸九鼎,象九州。”夏禹铸九鼎,以鼎象征九州,象征国家权力,后以鼎为传国之宝。《说文·鼎部》:”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象析木以炊,贞省声。”初为烹器,但后改用盛性之器。鼎的形制较多,一般略分为圆鼎和方鼎两大类,圆鼎在商周之际,盛行于世,方鼎行于商及西周初期。鼎卦形成始末,莫能知其究竟,然而,对宝鼎而言,确有其审美视角和价值取向。鼎为三足,三足平衡支撑而立,可稳妥,持之以恒,象征安泰,稳重,严肃,可以永恒于世。鼎卦的卦辞为六十四卦中仅仅是三字,为《易经》最短卦辞,释文是:”鼎,元吉,亨。”乃象征大吉大利,亨通万事之意,是有祈吉纳福之兆鼎卦,在诸卦中是一条吉利祥瑞卦目。所以,古代为利取吉祥,对此卦锺爱至甚,备加偏爱。于是,鼎卦就与数字”三”结下了不解之缘,再加前述原因种种,自此构成”三”的表现形态,演绎出了许多以前置”三”的文化层位统括法。诸如:三皇、三王、三君、三公、三官、三甲、三代、三宫、三神、三辅、三秦、三山、三江、三仰、三孔、三清、三锡、三、三已、三生、三巴、三舍、三竿等。撷取吉祥之说,在古代一脉相承意识支撑着及统合着较大比重人们思想的宙宇观,形成了传统观念及文化现象。尤其,儒释道三教兴起传播以后,对社会影响日益深远,起到如影之随形,究响之应声的作用,在社会中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潜移默化的形态,无论是生活琐事、日常习惯、风土人情、风情民俗、迎朋宴宾柳或赛社神祭、庙台演出、瓦舍勾栏演出等无不一一体现。正由于此,作为人类较为关注神秘数字”三”依其始终发挥着统合观念、组构思想的构素作用。从这一概念出发,戏曲中的”打通”为什么多数剧种必须是”三通”,势必是这种思想内涵的延伸,其结果影响应该是衍伸发展深远流长。
多门类的戏曲演出农村乡镇戏曲演出,或神礼庙台演出,或搭台建棚演出,皆初源于神诞赛会聚集。
北宋·朱《萍洲可谈》卷三说江浙地域多”以傀儡乐神,用禳官事,呼为弄戏。遇有系者,则许戏几棚,全赛时张乐弄傀儡,,,至弄戏则秽谈群笑,无所不至,乡人聚观。”这种现象不仅于江浙,其他地方亦有所存在。
如:山西万荣县孤山风伯雨师庙的宋元戏台,戏台石柱上就刻有”尧都大行散乐人张德好在此作场”的字样。题字时为元大德五年(1300年),这一遗迹,真实地展示张德好在神诞庙台演出的实录。
与神诞庙台演出,庭院场院,堂会或演出不悖而行,构成不同形式的演出方式。如河南新安县石寺乡李村宋墓即是一例。其墓主是宋四郎,墓为单墓室砖砌仿木结构。墓门是砖砌门楼,上端镶砌有一块铭砖,刻字为”宋四郎家外宅坟,新安县里郭千居住”并镌刻”砖作人贾博、刘博,庄住张窑,同共砌墓,画墓杨彪。宣和八年二月,(宣和为宋徽宗的最末一个年号,在历史上宣和仅有七年,”宣和八年”应为宋钦宗赵桓的”靖康元年”(1026年))墓内有多幅壁画如夫妻对饮图、庖厨图、交租图、双扇段窗、牡丹花卉及杂剧演出图等等。尤其,杂剧演出壁画,给我们提供了当时演出实况的记实,并将宋代副净与副末插科打诨、滑稽调笑舞台形象展现于世,体现到宋金杂剧院本向元代杂剧过渡发展的脉络轨迹及其形或发展规律。
神诞庙台演出、庭院场院演出两种不同演出方式,必然产生演出的不同风格。前都出于露天旷场演出,唱腔势必高亢激越,音感强烈;表演粗犷豪放,不易过细;化装浓妆盛抹粗线条,便于远观。后者出于庭院场院作场多为近景,相比之下,唱腔较为和缓平静;表演入微细腻,化装美观考究。鉴于表演方式之别,营造出诸多不同特色。所以,庙台演出,特别在音乐伴奏,则必须加上大锣大鼓配之喧闹,才可以达最佳舞台效果。”打通”是昔日演出不可缺少的演出程序。尤其,在露天舞台演出更具有实用价值,以后,随着都市现代发展现代化的封闭式剧场出现,”打通”失去其存在意义,逐渐退出历史进程,销声匿迹,不复存在。但,今日边远山区乡镇及农村露天剧场演出,仍有必要运用这种”打通”习俗,并且现在仍然使用。
“打通”在我国众多剧种中多有这种文化现象存在,但名称不一,如扬州戏称”打闹台,唱出头”,安徽除称”闹台”外,还称”闹花头”,四川称”打开台”或”闹台”,山西称”吵台”,云南称”三吹三打,加排鼓”,清末昆剧有”开场有三跳”之说,三跳即跳加官、跳财神和报台。
打通一般是三通,然而,亦事有例外,如山西梆子剧种除称”吵台”、”打闹台”,尤如梆子多是打”头通”和”二通”。打”头通”时,只是一般武场演奏员演奏既可,但当打”二通”时,必须鼓师和全体武场,全力以赴,极具水平,以中路梆子的”二通”,多有”花二通”之誉,驰名于世。京班”打通”有”苏通”和”高通”之别。
“苏通”是指昆曲班、安徽班所用通序乐点;”高通”是指高腔班及京腔班所用通序,即基本上是弋阳腔体系之乐点。从现存资料所载”二通”奏是少数,多数为”三通”奏。其”打通”目的,无非是对观众礼谊之敬,吸引观众静场,暗示演员进入角色,使演职员作好演出准备,使一般演员练唱调嗓。
前台鼓乐,三奏三擂,无论”苏通”,或是”高通”只是乐点有区别,但二者俱是单皮鼓指挥起乐,并大锣、小锣、铙钹共奏,初以简单锣鼓经乐点引奏开始曲(即”头通”)约有齐奏一刻钟,间息片刻(大约十分钟),继而奏响”二通”,乐点较前通复杂,并增添唐鼓齐奏,乐点有”急急风”、”冲头”、”走马锣鼓”、”抽头”、”九锤半”、”马腿”、”大水底鱼”、”收头”等等。这通演奏必须协调和谐,火炽喧腾,气氛热烈,气势磅礴,显示出戏班的演奏水平,以达到招徕观众之目的。再休息约十分钟,接奏”三通”,”三通”以唢呐为主,又称之为”吹通”或称”吹台”。”吹通”主要用唢呐多奏喜庆祥和迎瑞纳福的曲牌,曲声缭绕,联套有序,给以跌宕流畅酣畅淋漓之感。曲牌有[将军令]、[哪吒令]、[柳摇金]、[水龙吟]、[傍妆台]、[一技花]等吹奏曲,待”三通”完奏后,即为正戏演出。
周育德先生《中国戏曲文化·戏曲文学的返朴归真》云:”任何文化现象都表现为一个进程。
一个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更新,自我建构的过程。中国戏曲文化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宋元戏曲本来是一种俗文化,这在戏曲文学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明清时代,文人剧作家对这种俗文化进行了否定。文人传奇和杂剧使戏曲由俗变雅。到了清中时,雅戏曲走上了末路,以”乱弹”戏为俗称的真正的俗的戏曲蓬勃发展,再一实现了戏曲向俗文化的回归。”戏曲文化是一种俗文化;是一种文化的民俗现象;是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而且文化较潜隐不露的一种民俗文化轨范;是过去千秋万代百姓庶民创造和享用的生活文化;是民族的可贵精神遗产和宝贵财富。但,学士大夫视其为”小道”,认真不能登大雅之堂,鄙夷不屑一观。然而,作为俗文化的中国戏曲文化对社会影响是巨大,起到了潜在的作用。
戏曲与其它俗文化一样,都是在不断地自我否定,不断地自我更新,建构自我的形成体系,从而成长健全壮大发展。在一个社会群体所创造和享受的文化,既是这一社会群体的特有财富,又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打通”习俗体现了这一规律。虽然仅是一种文化形态,但对社会仍是一种可珍贵的东西,在今日应说仍有借鉴价值。在戏曲演出中,为了扩大影响,凝聚观者,展示阵容,露现水平,走向商业市场经济,分明是一种宣传媒体运作的有效形式,创造出雅俗共赏更新的途径,兴许恰恰是”俗化”的归真。
在知识领域中,不但要重视各种先进学科知识,也要重视人民自身的知识现状及其创造的历史财富,戏曲文化也是这种历史财富中的重要部分,虽然某些形态已成陈迹,但不可遗忘,要成为后人美好的回顾。
 范海龙新作展
范海龙新作展 崔明涛
崔明涛 “画水者”李
“画水者”李 “EXIN亚洲实
“EXIN亚洲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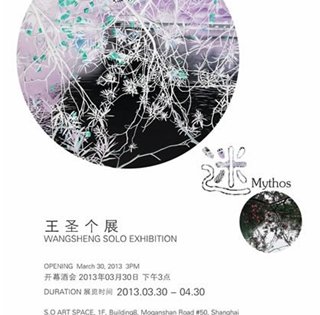 “迷Mythos”
“迷Mytho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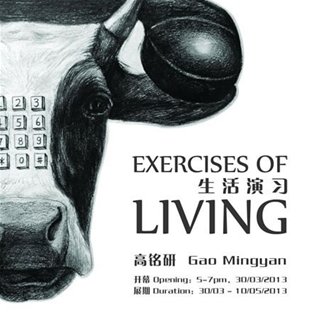 “生活演习”
“生活演习” “中国娇子”
“中国娇子” 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 中国戏曲
中国戏曲 北昆耆宿
北昆耆宿 潮剧的演
潮剧的演 景物造型
景物造型 服饰造型
服饰造型 戏曲文物
戏曲文物